
在理性詞典裡,心靈感應,可能是不存在的。它們不符合唯物論,不能用現代物理學和行為科學等科學原理和定律推導。科學要質疑的是:如果這種能力存在,它是怎麼實現的?有什麼場?通過什麼物質傳遞?
正是這些問題,忙壞了相信心靈感應的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們。他們從物理學、生物學、腦神經科學等多個學科尋找依據,甚至希望在量子力學中有突破性的進展。然而,說服力還是太微弱了。“最顯著的科學進展是以科學超越或否定人們的普通知覺和直覺為特徵的”。多少年來的局面一直是:科學佔盡上風。
但是,對超心理現象的探索卻從未停止。有數個假說被提出來,也有數不勝數的個案報告出來。不管科學與否,超心理學家們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
■ 心靈感應到的負面事件更多

1897年,詩人阿爾佛雷德·繆塞和兩個朋友在巴黎市區散步。他們歡快地交談著。在經過盧浮宮的售票窗口時,繆塞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你們沒聽到什麼嗎?有一個聲音在說’我在沙巴奈路被殺了!’”兩個朋友大笑起來,但繆塞看上去是如此害怕,他們決定到事發地一探究竟。在沙巴奈路街角,他們看到:有人抬著擔架,上面躺著一個剛被謀殺的年輕人……
超心理學家們認為,在出現心靈感應的多種形成因素中,精神緊張是最重要的一項:面對壓力或強烈的感情,一些人沒有用語言或肢體表達,而是不自覺地將其釋放到周圍的環境中去。於是,感受力強的人就接收到這一信息。這也是為什麼心靈感應到的事件,總是和事故、災難等負面事件有關。
人們所體驗到的心靈感應的事件,往往是與親人、戀人之間的。超心理學家們相信,在有著特殊感情的人之間,易產生心靈感應。感情越深厚,越容易通過“特異功能的渠道”傳輸。這是法國詞曲作家讓-皮埃爾·朗的故事:“在我妻子出外旅遊的一個晚上,大約深夜兩點,所有她的鏡框都在同一時間掉下來摔碎了。我被聲音吵醒了,面對破碎的相片,我確信我們要離婚了。當她旅行歸來,她就宣布了她要離婚的決定。”
■ 每個孩子可能都超驗

孩子們具有很強的心靈感應能力,年齡越小,這種能力越強。生物學的一些發現提供了部分支持。動物們普遍存在著對“外激素”即“信息素”的感覺,外激素是動物分泌的化學物質,這種物質能影響同類的行為。人類也擁有外激素,但接受外激素的器官鼻犁骨已高度退化,只有在胎兒和新生兒中,還有明顯的鼻犁骨結構。
這是俄羅斯心理學家們收集到的一個母親的見證:“當時,孩子正在我經營的商店門外的推車中睡覺,突然他瘋狂地尖叫起來。我趕緊把孩子抱起來。緊接著發生的事情讓我特別後怕:我剛把孩子抱在胸口,一個醉酒的司機就把嬰兒車撞翻了!”

33歲的編輯楊柳說:“四歲以前,我總是能夠聽到很多聲音,我也能看到很多的情景。我說給父母聽,但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四歲之後,楊柳變得“正常”了。在一個不反對超常現象的家庭中長大的人,有更多發展心靈感應能力的可能性。多數家庭卻過早地用成人世界的規範扼制了孩子的這種能力。隨著我們長大,感應能力也就消失了。
研究發現,藝術家接收特異信息的能力比普通人强两倍!法國心理學家埃里克·皮卡尼解釋說,因為他們“對情感保持坦率,對新事物充滿熱情,他們對想像中的事物從不心存恐懼!”或許,這正好解釋,為什麼保持著旺盛創造力的藝術家們,身上總是散發著小孩子般的天真和瘋狂。
■ 中國人更迷信?

不管科學的爭論如何,即使我們沒有特別的心靈感應能力,大多數的人仍然願意相信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菲力浦·莫里森認為,這是我們自己的需要!在《怪異與科學》一書裡,他寫道:“影響人們準確領悟的是人們過於重視巧合,並把巧合與事實混為一談的傾向。巧合常使人們感到富有戲劇性、奇怪和迷惑。沒有什麼事情真正需要解釋,需要解釋的僅僅是觀察者主觀的要求。”
人類一般具有輕信傾向,還有對於奇蹟的崇信。“中國人可能更容易陷入對於奇異現象的熱情中。”心理學家朱建軍說。2005年,中科院的一份權威調查顯示,在中國,每兩人中有一人信求籤,每四人中有一人信星座,每五人中有一人信周公解夢,但每50個中國人中只有一人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
未知的大自然,浩渺的宇宙,有限的生命,都讓我們內心深處有恐懼感,東明心理諮詢中心的劉明博士認為,“人們期盼奇蹟,甚至希望擁有這樣的能力,以消除這種恐懼。”
而對於奇特事情的發生,我們如果找不到可以解釋的理由,就會焦慮,“為了找回這種控制感,我們就會說服自己,編一些理由來合理化該事件。心靈感應就是其中的一種方法。”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肖震宇說。
■ 從心靈感應中得到樂趣

很多相信心靈感應的人,也並非真的相信,嬉戲的成分遠大於此。生活中每天都發生很多讓人眼花繚亂的事,但那是全世界加起來的數目,相對於我們自己,生活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心靈感應,拋開了我們賴以理解世界的因果關係,給平凡的生活帶來了強烈的戲劇性。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的,太科學,就剝奪了眾多享受的可能性,而選擇相信,就像是暫時擺脫理性的束縛,沉浸於無聊的誘惑和開心之中。
相信的樂趣就是一種積極的心理暗示。李濤和劉婷兩個人經常同時給對方打電話、發短信;一起去登長城的那天,他們聽到太多的喜鵲在四面八方叫著,這被當作了好預兆,“是神的祝福”,他們不約而同說起了結婚這件事!在親密的伴侶中,多數人會擁有類似心靈感應的體驗。這樣的“感應”,會讓人對彼此的關係有越來越好的預期。
■ “它是命運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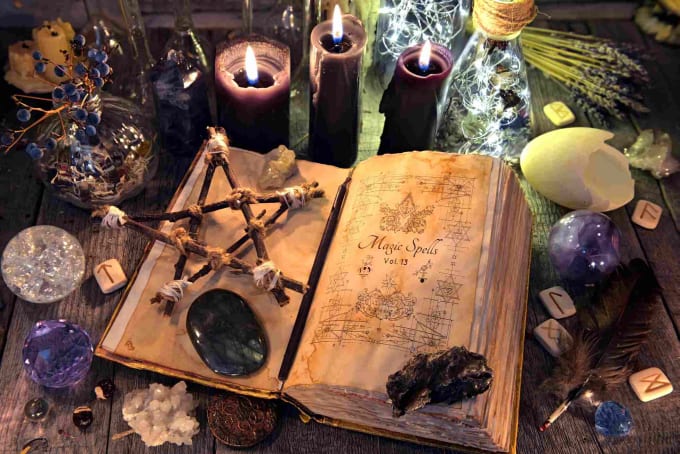
哈欣的男友出差了。一天,男友送她的耳環突然墜地,一種瀰漫著的不安的情緒包圍了她。“我們的關係要完吧?”對於哈欣的不安和追問,男友一概否認。但最終他們還是分手了。男友承認,就在哈欣耳環墜地的那一天,他與另一個女人一見鍾情。
“在他們關係非常好的時候,耳環掉下來,她只會去找首飾商解決質量問題。但現在,她內心的現實是:對這段關係沒有安全感。於是她格外注意與男友相關的具體事件。掉耳環,就能確定他們關係的方向嗎?這不過是把關係的破裂推給命運,說服自己放棄,也讓自己免於嚴厲的自我評判。”首都師範大學心理諮詢中心主任藺桂瑞說。
“喜鵲總是要唱歌的,耳環總有壞的時候。是我們主觀地選擇了這些外在的事件,以為它驗證了自己的想法或是決策。”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更會傾向於認為,不該違抗這種神秘力量。藺桂瑞認為:“事件可能加深了人們彼此對這段關係的信念。但這其實正是他們自己的願望。”
■ 我們是“迷信的鴿子”嗎?

心理學上有一個經典的研究:把鴿子放到籠子裡,隨機地投放食物。如果鴿子正好在投放食物時抖動了一下羽毛,或者伸展了一下翅膀,那麼當後面再出現這樣的巧合時,鴿子就會認為它們自身的動作與獲得食物有關。
就這樣,它們會為了獲得食物而不斷抖動羽毛或伸展翅膀,變成“迷信”的鴿子。
就這一點而言,我們人類並不見得比鴿子高明多少。那些看起來神秘的事件,我們認為它不可解釋,很可能是我們對它的背景了解得不夠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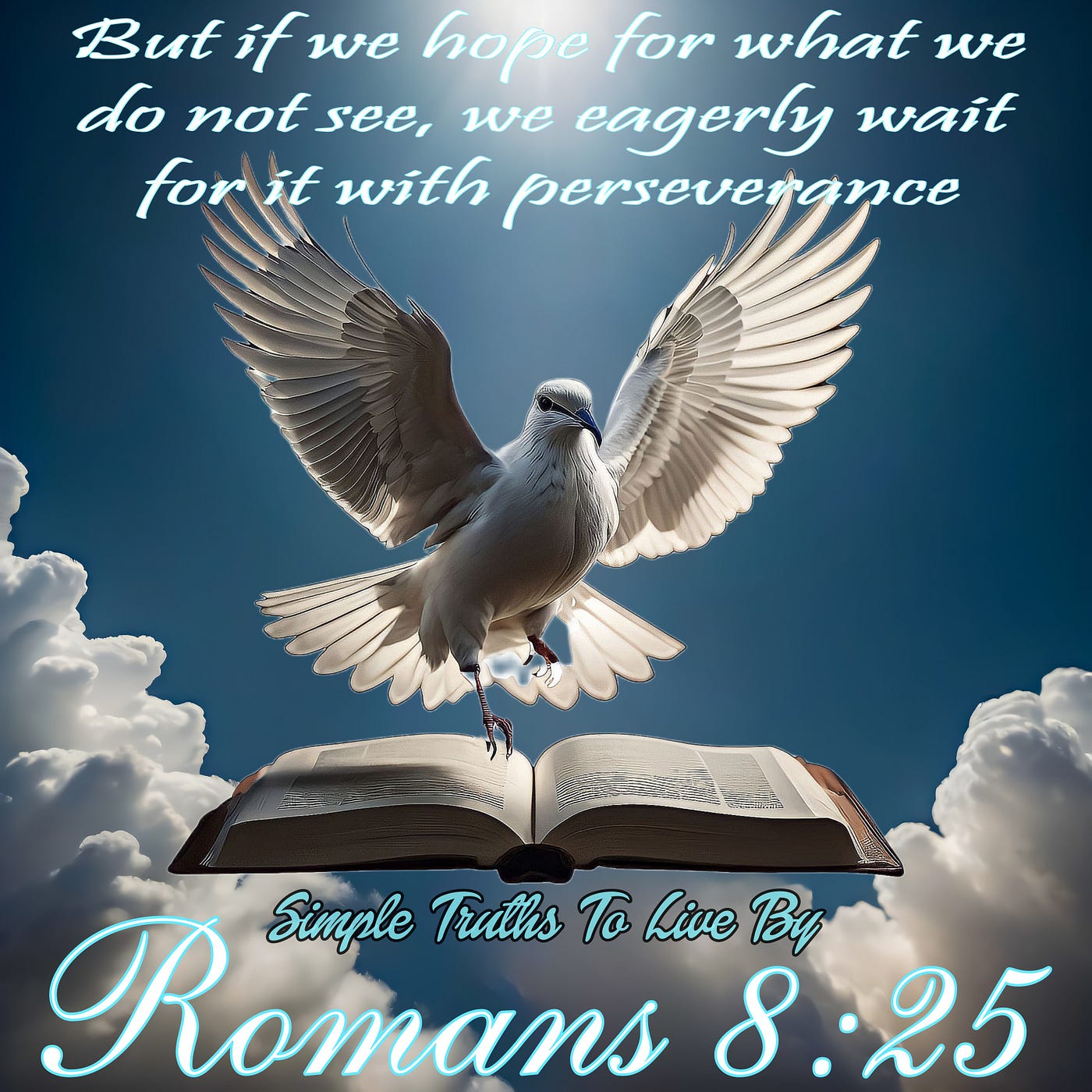
我們的記憶也是很有意思,它“選擇性”地記住了那些巧合的事件,哪怕它只有一件。而大量的未曾應驗的,我們統統不記!有個有趣的說法:“受傷的指頭總是被人碰”。這是為什麼?因為你格外注意它!

